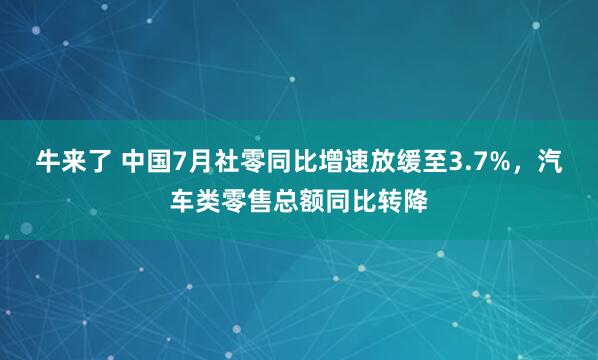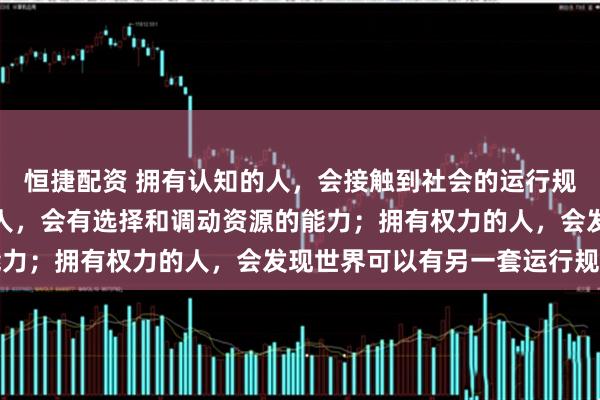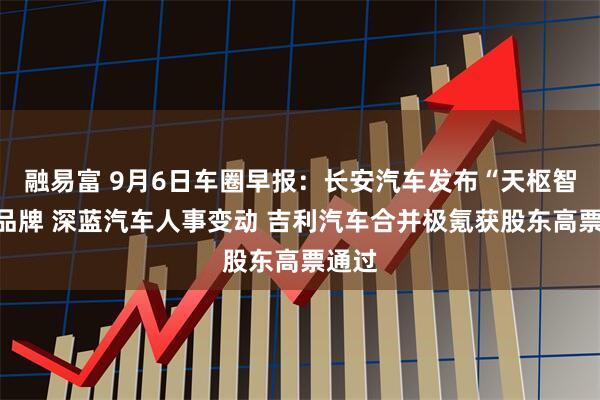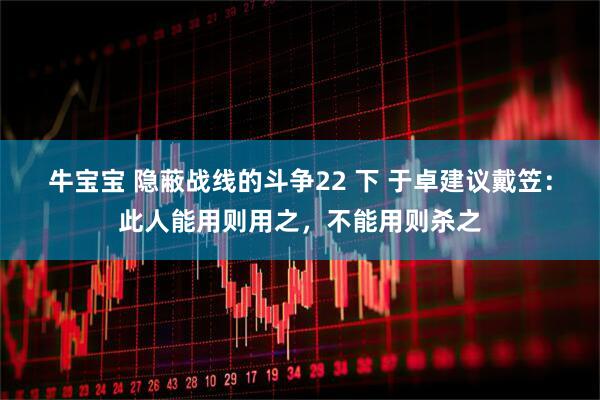
1937年3月上旬牛宝宝,《真理报》发表了一则消息,说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将军已恢复了自由,并乘飞机去太原接洽重要问题。
组织上迅即交给于炳然一个新的任务:返回国内,帮助张学良将军巩固 东北军,以使之成为抗日的一部分力量。于炳然归国后,才知道这一消 息乃是误传。
6月28日,为筹集办东北救亡总会机关刊物的资金,经高崇民、卢 乃赓写信联系,于炳然在上海晤见了张学良将军的女友赵(赵四小姐)。
见面后,赵说,两天之内她就去看张学良,要于炳然写一封信由她带 去。于炳然在信中赞扬张将军“双十二”之举为民族建立了功勋,又将 东北救亡总会成立的情形和要办一种刊物的打算告诉了他。
7月初的一 天,赵来电话约于炳然在虹口摩里根饭店会面。见面后,她说:“汉卿 特别关心你,赞成你办刊物。但要慎重,不要像杜重远似的闹出事来。 最好现在不要活动。等汉卿出来后, 一切都有办法。”
接着,她拿出 2000块钱说:“这是给你办刊物用的。不够,以后再向我说。但无论如 何不要说是汉卿给的,必要时只能说是我给你的。”
东北救亡总会的 《反攻》半月刊就是于炳然用这笔资金办起来的。
1938年秋,即武汉失陷前夕,为了救济流亡在关内的东北难民,于 炳然代表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,向被关押的张学良将军募捐。张将军慨 然应允,并亲笔写信让王化一为之解决——张将军捐赠了3000元巨款。 此后,张学良将军长期被监禁,失去了自由。然而在于炳然的心中, 一 直深念着这位和他在抗日救国战线上结成不同寻常的情谊的朋友、这位 为全民族同胞所敬仰的伟大爱国者。
舌 战 戴 笠
1937年5月,于炳然从莫斯科回国后,按照党组织的决定,在上海 的一家旅馆和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会面了,从而与党接上了关系。 潘汉年要他以东北籍归国留学生的身份,去南京面见蒋介石。
于是,于炳然去见了蒋介石。他不卑不亢,从容恳切,着重谈了政府应支援东北 抗日联军和恢复张学良将军自由的问题。
不久,经上级党组织同意,于炳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二处设计 委员、少将参议。从此,他以这一职务为掩护,长期从事党对国民党上 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党的地下工作。
西安事变后,蒋介石派戴笠(以他秘书的名义)来对付东北军和所 有的东北人。其目的在于防止东北军反蒋,并相机拉拢东北人士为蒋所 用。戴笠与东北人的一切交往、应酬和监视,无不出于这一用心。
1938 年4月,戴笠与于炳然曾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。
见面后,互相寒暄了几句,戴笠就把话转入正题:“炳然兄,咱们 做个什么样的朋友,普通朋友还是特殊朋友?”
于炳然反问:“什么是普 通朋友?什么是特殊朋友?”
戴笠说:“普通的朋友,你有事,你求我; 我有事,我求你,这叫普通朋友。至于特殊朋友,那就不同了,我马上 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好朋友,很重要的好朋友,而且可以使你马上负起一 部的责任。”
于炳然又反问:“雨农兄,你看我够一个普通朋友,还是够 一个特殊朋友?”
戴说:“如果你仅够个普通朋友,今天的话我就不说 了。”
于炳然说:“那很好,我当然高兴做你的特殊朋友。”
戴笠神色诡 谲地说:“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。当你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,于卓(当 时驻苏大使馆武官)曾给我一封电报,其中说你有四个优点:
第一是富 有国家与民族思想,
第二是为人精明强干,
第三是很有吃苦耐劳精神,
第四是很重义气。
但另一方面你的思想左倾,在莫斯科曾与王明有来 往,恐系共产党员。
他的结论是:此人能用则用之牛宝宝,不能用则杀之。”
戴笠掷出“杀”字后,注视着于炳然的神色。见对方并无任何反应,他 又做出微笑来,接着说:“当我接到这封电报时,我曾很费思考。这样 一个好人,又有国家民族意识,又精明强干,又能吃苦耐劳,又重义 气,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呢?
我想不外是三个理由:
第一,他主张抗日,政府当时还没抗日,所以他反对政府,因而加入了共产党。但是, 政府是主张抗日的,当时所以不抗日,是在争取准备的时间,到了抗日 的一天,自会得到谅解。所以这一条是不成问题的。
第二,他政治上无 出路,所以才加入共产党,那么给他出路。所以我看这一条也是不成问 题的。
第三,也许他是个理论上有修养的人,认为救中国的办法,三民 主义还不够,必须共产主义。那么,既然是个理论上有修养的人,当然 知道中国并不是个资本主义国家,不能实行共产主义,所以我看这一条 也是不成问题的。
因此,我看到于卓的电报,又加以思考之后,我只想 了那个'用’字,没想那个'杀’字。
现在我们认识快一年了。据我的 观察,于卓说你的四点长处,都是事实。因此我想,他说你'恐系共产 党员’,也不会不是事实。
现在这样,你在《大公报》上登个'郑重启 事’,说你从未加入共产党,或是脱离共产党。只要你这样,我到委员 长那里,保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来。”
于炳然一面泰然自若地听戴笠 的话, 一面在考虑应付办法。
戴笠说完之后,于炳然从容不迫地问他: “你愿不愿意你的特殊朋友,在社会上闹到人所不齿的地步?”
戴笠说: “当然不愿意。”
于炳然说:“那么假如明天我在《大公报》上登个'郑重 启事’,说我于炳然不是共产党员;后天,人家在《新日报》上登个反 问启事,说某某人声明不是共产党员,但谁说他是共产党员了?无的放 矢,何其无聊乃尔!叫我在一般朋友中何言自解?
于武官说我的四点长 处,我虽然愧不敢当,可是我愿用以自勉。至于说我'恐系共产党员’, 这决非事实……
不错,在莫斯科我曾与王明有过往来,那正是由于我主 张抗日救国,我愿意知道共产党对于抗日救国的具体主张。况且,那是 在莫斯科,王明也没有怕与我会见及谈话的必要,所以才曾经见过面。
但不要认为与王明见过面的人就是共产党员……以你的权力,难道还怕 我吗?”
于炳然说话时,从容自然,理中藏锋。
戴笠听了之后,半晌没 有吱声。最后勉强地说:“请你考虑考虑吧。”
于炳然说:“事情在我这方面是很简单的,用不着什么考虑,还是请你多考虑考虑吧。”
为了达到把于炳然拉过去的目的,戴笠一面以“杀”相威胁,一面 以高官厚禄相引诱;表面上堂而皇之,彬彬有礼,实际则阴险狡猾,凶 狠毒辣。
于炳然对戴笠的一番威逼利诱,既无所畏,更不为所动,凭借 大智大勇和舌辩之才,巧与周旋,使戴笠奈何不得,只好收场。
奋斗在抗日救亡前列
1937年6月1日,于炳然到北平参加东北救亡总会(简称“东总”) 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。“东总”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 救亡团体。
它的任务是:
一、促使蒋介石兑现诺言,实行抗日;扩大民 族统一战线,拥蒋抗日。
二、营救张学良将军。
三、声援东北抗日联 军牛宝宝。
6月20日,“东总”成立大会在北平东北大学开幕。大会主席团由 高祟民、卢广绩、栗又文、苗勃然、于炳然5人组成。大会通过了简章, 选举了委员和常委,确定了组织机构。于炳然被选为常委,担任宣传部 主任。
卢沟桥事变后,“东总”总会迁到上海,上海抗战爆发,又迁到南 京。同年11月,上海沦陷,南京不保,“东总”按照周恩来副主席指示, 随国民党政府退到武汉,在武汉明月桥顺直会馆办公。这时,“东总” 党组,受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。党组书记为刘澜波,党组成员有张希 尧、张庆春、阎宝航、韩乐然、陈先舟、徐仲航、于毅夫和于炳然。
1938年1月的一天,刘澜波通知于炳然,说王明(中共中央长江局 书记)要来看于炳然,要他晚间在旅馆等候。
深夜,王明和潘汉年一同 来了。于炳然向他们汇报了回国后的工作情况。王明征求于炳然对今后 工作的意见,于炳然表示,愿意回党内工作,不愿再搞统战工作。
王明 考虑后,表示同意。
而潘汉年却说:“像炳然有这样的社会关系和活动能力,还是在外边工作好。因为我们能胜任这样统战工作的干部是不多 的。”
王明觉得潘的意见有理,就表示同意。
1938年6月,“东总”成立一周年之际,经改选,于炳然担负了更重 要的责任——总会秘书长。从此,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“东总”的工作 上了。
当时,在武汉的许多救亡团体中,“东总”被称为老大哥。它有14 个分会,30多个通讯处。它支持和组织了抗日武装——游击队,在武汉 曾开办过几个训练班,把培训的干部分批输送到华北各游击队中。“东 总”还先后组织了三个战地服务团(即文工团),先后送往吕正操部队 和延安。
在武汉,“东总”的宣传队和群众游行队伍,是最引人注目的。不 但参加的人数多,而且队伍中有色调鲜明的彩旗,有巨幅的漫画和宣传 画,有整齐的乐队和歌咏队,有加以装潢的宣传卡车。“东总”的宣传 队曾在汉口公演了三天抗战戏剧,颇得好评。
这些宣传形式,大部分是 于炳然从莫斯科借鉴来而加以创新的,它很快被各救亡团体所效法而推 广起来。在文字宣传方面,“东总”的《反攻》半月刊是当时一种很为 人注意的刊物。“东总”还举办过多次“名人讲演会”和“抗战问题座 谈会”。
1938年秋,武汉撤守前,国民党政府决定政治中心设在重庆,军事 中心设在衡阳。“东总”也大体上随着这一形势而部署。
决定以高崇民、 刘澜波为首,携同组织、训练、联络三个部和一个宣传队去西安;
以阎 宝航、于毅夫为首,携同秘书处、宣传部全体人员去重庆;
以于炳然、 刘亚光为首,去衡阳。
要联合两广湘赣各地会员和东北同乡,创立一个 规模宏大的东南分会。
在撤退前夕,于炳然按照党的决定,搬到李杜那里,正式就任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。
于炳然随李杜及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人员, 一路乘汽车经长沙奔 赴衡阳。到衡阳后形势已大变,便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退至桂林。
到了桂林,于炳然接到阎宝航、于毅夫的来信,约他速去重庆,并 说军委会已决定成立“战地党政委员会”,由李济深主持,李杜有可能 被任命为常委。为了促成此事,李杜委托于炳然前往活动。于炳然于12 月28日乘机飞往重庆,他的活动取得了成功。1939年初,李杜被任命为 战地党政委员会专任委员。不久,经李杜推荐,于炳然被该委员会任命为设计委员。
于炳然和李杜的友谊是从1933年春开始的。
1933年4月,于炳然正 在巴黎出席旅欧华侨反帝大同盟的各分盟代表大会。忽然接到刘咸一 (共产党员)、杜春晏的电报,约他速去柏林。于炳然从报纸上得知,著 名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、李杜、苏炳文,已于4月10抵达柏林。于炳然 猜测,约他前往必与此事有关。
果然,到柏林后知道,刘咸一所以发 报,乃是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领导人王炳南的授意。因为马、李、苏三 人到柏林后,已为中国公使馆派一批人包围起来,使进步留学生无法与 他们接近。只有刘咸一、杜春晏,因是黑龙江人,还可以经常在马占山 等几位将领的左右。约于炳然前来,正是为了加强对三位将军的影响。
在柏林的十几天中,于炳然与李杜相处得较好。李杜对国民党有强 烈的不满情绪,很愿意同于炳然交谈。后来李杜去罗马,又特地约于炳 然前去。在罗马,于炳然与李杜同住了多天,他们每日必谈,而且见解 略同。
有一次于炳然问李杜:“你所领导的义勇军,为什么不联合共产 党共同抗日?”
李杜支吾了半晌,不知如何回答。实际上,这一问,使 李杜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震动,使他思想上由于国民党的宣传所筑起的 反共堤坝,开始动摇。临回国时,李杜特地向于炳然表示,他回到上海 后,希望共产党派人与他往来。
在重庆期间,于炳然与在重庆的东北上层人士如李杜、刘哲、莫德惠、邹作华、万福麟以及王亢生等经常往来,相处甚好,因而常取得他 们对“东总”工作的支持。
例如,当时“东总”经费相当困难,甚至连 许多同志的最低生活费用都难以保障。于炳然就曾经每月从李杜那里拿 来三四百元钱,给刘澜波、于毅夫、陈先舟、徐仲航、张希尧、韩乐然 等同志作生活费用。
为曹松华、车向忱以及赵清黎、卢广声同志的生活 和“东总”工作上的需要,于炳然曾找过王芃生帮忙。但于炳然本人却 从不接受他们的帮助,那是为了留一条替别人、替“东总”说话的后 路。
李杜将军对于炳然是极为信赖和器重的。他曾把张学良将军赠给自 己的一支派克金笔转赠给于炳然作纪念,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之深了。
功 不 可 没
于炳然从1937年经党组织同意,打入国民党上层,任军事委员会第 二处设计委员、少将参议开始,直至1941年奉命撤回延安为止,除了做 党的统战工作外,还一直以他的特殊身份,从事党的情报工作。
1939年8月,于炳然按党组织的部署,正式到“国民党军委会战地 党政委员会”就任设计委员、少将参议。该会下设军事、党务、政治、 经济、文化和敌情六个研究组,于炳然任敌情研究组组长。
因此国民党 “军统”、“中统”、“国际问题研究所”的各种情报,在于炳然手边都有一 份。他把这些情报,及时地让人复写,送交给我党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的王梓木同志。
有时,对成册的、系统的材料,复写来不及,于炳然就 把原件送交给党组织,待用完后再退还。当时在重庆,国民党的特务活 动是无孔不入的。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以及从那里出入的人,都时 刻在特务监视之下,所以传送情报一事必须格外慎重。当时于炳然所提 供的情报,多数是王梓木以看望老同乡的名义,到“东总”来取。对于 特别紧急、重要的情报,只得采取其他方式来传递。
如有一次,于炳然先用电话约好,双方各驾驶一台汽车,在约定好的时间、地点相遇。在 两车相错的一刹那,把情报送过去了。
凭着卓越的胆识和机敏,于炳然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,始终隐蔽得 很好,不仅没被敌人所察觉,而且就连同他一起在“东总”工作数年的 同志,也丝毫没有察觉到他秘密地在另一条战线上还从事着工作。
1939年10月以后,“东总”的活动开始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限制。 《反攻》半月刊连遭刁难性审查。各地分会遭到的打击更大。
鉴于这种 形势,1940年7月初,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于炳然和于毅夫二人撤离重 庆。偏巧这时战地党政委员会改由程潜负责,李济深被调往桂林任行营 主任。于炳然征得周恩来副主席同意,趁李济深离职前,先行撤退。
于 是,他向李济深呈请,去陕北榆林,视察东北挺进军的伪军反正工作。 他的呈请得到准许,并同意他携带副官和秘书各一人同往。
出发前,于炳然遵照周恩来副主席指示,将他的可能利用的社会关 系全部留下。他将李杜的关系介绍给于毅夫;将王芃生的关系介绍给徐 仲航;将屈映光的关系介绍给阎宝航。
临行时,周恩来副主席对于炳然说:“共产党人,走到什么地方都 要把屁股擦干净。你既然说是去马占山部队,就去一次,将他们给你的 任务完成后,写个报告,算清了报销,回到延安再留下,派你的秘书回 来办交代。不要一到延安就不去了,免得他们又闹什么'携款潜逃’ 啦、'通缉’啦等名堂。到延安后住交际处,刘澜波去看你,你再同他 商量北去的事。”
周副主席又说:“到西安后,办一件事,高崇民生活已没有办法, 林老(伯渠)几次给他钱,他不接受。你要说服他,哪有只管工作,不 要生活费的道理,一定要他接受。”
于炳然以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视察员的身份,率秘书张石光、警卫员唐昆,奔赴陕北。
到了西安,于炳然去见林伯渠同志。林老建议他随马占山的运输队 走,比较安全。于炳然已将高崇民说服,并从林老那里为他代领了三个 月的生活费。又与高崇民商定了今后西安分会的工作方针。
于炳然一行三人,随马占山运输队长途跋涉,于10月20日到达了 他们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——延安。他们在延安只停留了10天,就按照 周副主席的指示,继续北上,奔赴榆林。在那里完成使命后,于1941年 1月15日返回延安。
同年4月,中央组织部分配他到马列主义学院和马 列主义研究院学习。8月,他被分配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,任国际组 组长,受任弼时领导。在此期间,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单独接见。1942 年3月,调到中央情报部第四室,任调查研究组组长,代理第四室副主 任。
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时,隐藏在党内的大阴谋家康生,直接掌握反 奸肃反的大权。他利用窃取的权力,对许多党内外的好同志、好干部, 进行残酷斗争,无情打击。
在所谓《抢救失足者》的报告中,他竟无中 生有,信口雌黄,说:“东北救亡总会是红旗特务机关”,“于炳然,准备好人,准备好枪(指与于炳然同来延安的副官和警卫员,以及他们随身 佩带的枪支),要与胡宗南里应外合,包围边区,进攻延安。”
由此,不 容于炳然以实情相分辩,把他押进了监狱。谁料这一入狱,竟达数年之 久,其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。
1946年,周恩来副主席得知于炳然所蒙 受的不白之冤,十分震惊,立即由重庆发回电报,证实了于炳然在他直 接领导下工作的真实情况。这样,于炳然才得以恢复了自由,恢复了组 织生活。
1947年,于炳然回到中央社会部(原情报部)从事研究工作。1948 年初,中央成立外事组,在平山西柏坡召开会议,由周恩来主持会议, 于炳然出席了这次会议。1948年底,于炳然由中央社会部派出,作为先 遣部队,随李克农部长进驻北平,进行接收工作。
1949年4南京解放,于炳然任南京公安局办公室主任。1949年月11月,重庆解放,于炳然率 少数干部进城接管,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情报处长。
重庆是国民 党政府最后的所在地,所以西南地区解放初期的敌情相当复杂。在肃清 匪特、维护社会治安工作中,于炳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1952年春牛宝宝,于炳然不幸逝世于重庆,年仅49岁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宝尚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